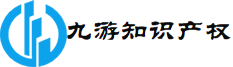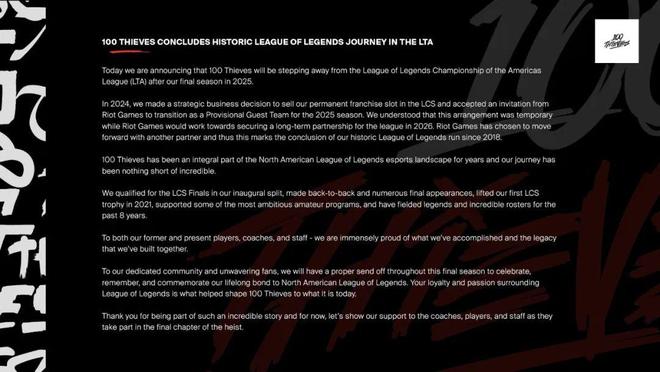咨询电话: 027-88109788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有了“绿色通道”!
发布于 2025-07-22 03:15 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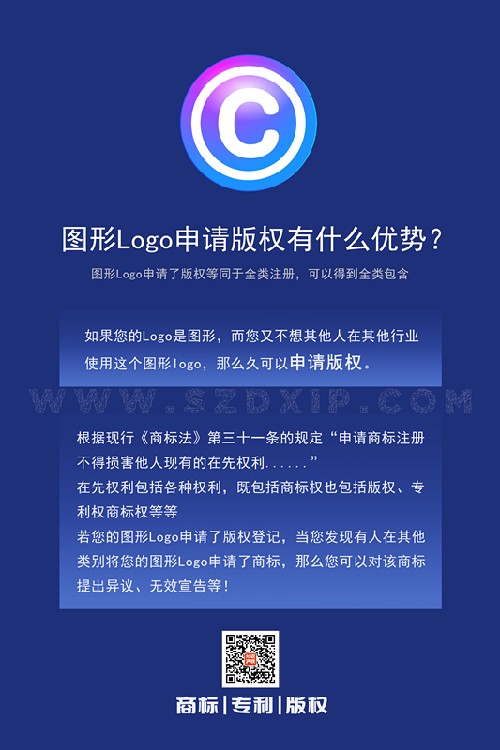
2025-07-21 14:58:41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5年第25期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起著作权侵权纠纷通过“小额诉讼”方式妥善化解。从立案到开庭审结仅用7天,以最快速度满足当事人的解纷需求,得到双方当事人的一致好评。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知识产权作为创新驱动的核心要素,其司法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知识产权案件固定证据难、涉外案件占比高、案件审理周期长、技术类案件查明难等问题困扰着权利人。为破解这一难题,我国各地法院通过机制创新,构建知识产权审判司法“绿色通道”,在批量案件快审、跨境纠纷速裁、程序整合优化等领域形成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实现了从机制创新到个案实践的全流程提速。统计数字显示,全国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持续增长,从2016年的17万件上升至2024年的近53万件,年均增速28.9%。与此同时,因为员额制改革,从事知识产权审判的法官人数,相较8年前不增反减。面对迅猛增长的案件与审判队伍精英化之间的矛盾,推行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强化程序的多元供给成为必然要求。202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并据此制定《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以此为起点,各地法院开始探索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机制,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产权审判提速改革拉开序幕。南京法院率先结合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审判特点作出尝试和探索。南京中院专门出台了《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的实施方案(试行)》,根据案件类型、案件事实、社会影响、所涉法律关系等特征,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分为简单案件和复杂案件。在明确案件繁简类型的基础上,由法院的立案部门根据诉讼标的、案件事实等特征,通过分案系统的技术性设置,分别确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我们的繁简分流改革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除了关注基层法院的快审机制以外,也充分考虑到南京中院审理的大量简单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如权属明确、事实清楚的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已经经过示范性诉讼的部分类型化维权一、二审案件等,都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适应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快审机制。”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姚志坚介绍道。统计数字显示,近三年(2022-2024)南京两级法院适用小额诉讼、简易程序和独任制普通程序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平均审理天数分别为30.2天、49.3天和144.7天,相比改革前同期分别缩短了21.2天、7.5天和66.6天,知识产权纠纷化解效率得到有效提升。重庆两江新区(自贸区)人民法院创新推行的知识产权小额诉讼审判模式,是司法系统针对长期困扰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痼疾,所给出的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该模式聚焦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知识产权案件,依托重庆法院“易诉、易审、易解、易达”的“四易”智能云平台,深度融合“自助式证据交换”“一站式网上办案”“要素式审判”等工作机制,实现了知识产权案件“快立、快审、快结”的司法效能飞跃。2020年11月,某知名动画形象“贝肯熊”的著作权人发现,一款安装量高达295万次的App未经授权提供了大量“贝肯熊”系列图片的搜索和下载服务。原告随即向重庆两江新区(自贸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1万元。由于当事人分处异地,法院通过电子方式送达诉讼材料,并引导双方使用“自助式在线证据交换平台”,在非同步、非实时的情况下完成举证质证。审判人员依托“易诉”平台居中调解,该案从立案到结案仅用了7天时间,原告仅承担20元诉讼费,不仅高效维护了著作权人权益,更显著降低了跨地域维权成本。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既是司法改革的产物,又肩负着推进司法改革、探索知识产权审判“中国样本”的重要使命。立足改革法院定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不久就开始探索构建商标行政案件繁简分流程序,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优质快捷的司法服务。2016年2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探索在立案庭设立速审组,对商标驳回复审行政案件实行集中快速审理。2021年8月,逐步将商标驳回复审行政案件、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二审案件等简单案件通过适用简易程序、要素式审判等方式集中快速审理。一系列数字见证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真正实现了商标行政案件的快慢分道、繁简分流,推动商标行政纠纷实质性化解。截至2024年9月底,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通过简案快审方式审结各类简单案件77357件。2023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用全院17%的审判力量高效审结了超过46%的相对简单案件,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平均审理时长同比缩短29.44%,商标驳回复审行政案件平均审理时长为87.59天,同比缩短36.48%,审判效率显著提升。武汉法院系统推行的“繁简分流”机制,是应对“案多人少”矛盾、提升司法质效的又一项系统性改革。2024年4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知识产权小额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在全市实行推广。法院将事实清晰、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较小且标的额在湖北省上年度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0%以下的知识产权案件,纳入小额诉讼程序审理,这类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制,旨在通过简化流程实现简案快审,九游体育官方平台为当事人降低诉讼成本;而对于专利技术类等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则归入“繁案”审理体系,由专业审判庭精细化审理,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类案专办”的资源优化目标。这一改革贯穿立案、审判、执行全流程,深度融合科技赋能与程序创新,显著提升了司法效率与群众获得感。2024年,武汉全市法院知识产权案件调撤率超过66%,平均审理时间同比下降22.32天,服判息诉率同比上升1.97%。知识产权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不仅是审判流程的优化,更是司法理念的升级。各地法院以繁简分流为起点,积极探索创新举措,推动知识产权审判效率提升明显,让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进入“绿色通道”的同时,也让公平正义跑出“加速度”,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力司法保障。许多企业的创新成果在案件审理和判决过程中,就已经被侵权产品凭借低价优势迅速抢占市场。即便这些企业最终通过法律途径赢得诉讼,也失去了原有的市场领先地位。如何帮助企业高效解决纠纷?占据京津冀这一地域优势的天津三中院给出的答案是,适用先行判决。原告是某净水器系统的专利权人,认为被告未经许可,大规模生产被诉侵权产品,侵害了其专利,于是将销售公司一并起诉至天津三中院,要求停止侵权,并综合考量被控侵权产品的利润、被告的主观恶意、侵权规模、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等因素,主张几百万元的赔偿。考虑到案涉的这两家净水器公司都是行业龙头企业,生产的产品占据了净水器市场的“半壁江山”。案件受理后,合议庭的态度非常审慎,仔细研判后认定该案是非常典型的技术类案件,遂引入技术调查官。最终,法院认定该案被诉侵权产品的技术方案落入原告专利权保护范围,构成侵权。此时,另一个难题摆在面前。由于侵权时间较长,被诉侵权产品的产销量较大,对于原告主张的损害赔偿计算方法及相关证据,比如销售数量、利润率、专利贡献比例等,都需要花时间查明。时间不等人,当时又恰逢“双11”电商节,产品进入销售旺季,如果等所有事实都查清后再判决,权利人的损失必然会进一步扩大。合议庭经过反复研究、认真合议,决定就已经查明的专利侵权事实部分作出停止侵权的先行判决。合议庭仍继续审理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原被告达成和解。原告获得了相应的补偿,被告通过支付一定的费用能够利用原有的生产线继续生产和销售已有的产品。“结局”皆大欢喜。早在2018年3月29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搜狗诉百度输入法”系列专利侵权纠纷三案中,首次适用我国民事讼诉法第156条,仅对“侵权成立与否”这部分事实进行审理,作出先行判决。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成立后,于2019年3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瓦莱奥发明专利侵权案。本案一审是原告瓦莱奥公司起诉卢卡斯公司等三被告侵犯其发明专利权,由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结并就确认侵权及停止侵害部分作出先行判决。后两被告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原审原告提出的立即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在部分判决的上诉审中,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当庭维持了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的“被告停止侵权”的先行判决。现在,越来越多的法院“以创新的方式保护创新”。在审理周期较长的知识产权案件时,在已经查明的知识产权侵权事实基础上,作出让被告停止侵权的先行判决,避免被侵权者合法权益在诉讼过程中受损继续扩大。但是,长期办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张律师认为,“先行判决”还未能达到让权利人及时止损的目的。“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即使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侵权并对其作出停止侵害的先行判决,但由于被告上诉,先行判决进入非确定、未生效状态,实际上没有产生强制执行力,被告侵权行为仍在持续。”她说,“这也是我国适用先行判决制度普遍存在的问题,即我国一审先行判决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不能充分发挥先行判决的实际功效,使其达到及时止损的目的。”如何使“先行判决”及时止损?在这方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知识产权法庭先行一步创新审判机制,进行了探索和尝试。2020年11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知识产权法庭在审理“大疆公司诉飞米公司、九天纵横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6条就已经查明的专利侵权事实作出停止侵权的先行判决,同时创造性地首次引入“先行判决+临时禁令”的裁判方式,使一审先行判决赋予执行力,以达到及时止损目的。一直以来,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侵权与无效宣告分属司法与行政两条线,存在交流壁垒,是制约知识产权“快保护”的一大掣肘。如何帮助企业摆脱这一羁绊,实现高效维权,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知识产权法庭积极探索知识产权侵权民事诉讼与关联确权行政程序的协调审理模式,力图稳定权利状态,提高司法保护效率,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以下简称“复审无效部”)、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以下简称“深圳保护中心”)深度合作,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区特色的联合审理之路。被深圳知识产权法庭“首吃螃蟹”的是一起名为“扩展坞”的实用新型专利纠纷案。时间回拨到今年4月,该扩展坞实用新型专利权人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被告侵害其专利权。法院受理案件后,涉诉产品即被电商平台下架,面临不小的经济损失。被告心急如焚,提起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希望尽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深圳知识产权法庭研判发现,案涉专利存在权利稳定性存疑且被告已提起无效宣告请求。复审无效部选择在深圳进行巡回口头审理,符合联合审理的适用情形。承办法官于是启动协同程序,并与深圳保护中心和复审无效部建立“双向沟通”:一方面就案涉专利创造性、新颖性判断标准与复审无效部对接,对案涉专利内容进行探讨;另一方面围绕侵权判定中的技术争议、侵权认定等问题,向复审无效部专业团队咨询,提前形成案件技术事实争议焦点的分析判断。5月27日上午,复审无效部合议组在深圳保护中心审理庭对涉案专利的无效宣告请求开展巡回口头审理,承办法官全程旁听,同步记录双方观点、捕捉双方分歧;下午,深圳知识产权法庭公开开庭对专利侵权案件进行审理,依托上午的确权结论当庭宣判,作出侵权纠纷裁判。深圳保护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这种审理模式,将以往需要数月的程序周期压缩至1个工作日,实现了专利行政确权与民事侵权诉讼程序的高效衔接,明显加快了专利侵权纠纷的化解进程。与深圳知识产权法庭不同,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采取统一审理技术类知识产权行政和民事上诉案件的“二合一”协同审理模式,实现了确权行政案件与侵权民事案件的同步审理、协调对接、高效解纷。据媒体报道,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受理了一起棘手的“大案”。该案由5件“案子”组成:4件是专利权侵权纠纷。A公司认为G公司侵犯其专利权,请求G公司赔偿2.67亿元。一审法院判决G公司向A公司赔偿合计约2.2亿元;另外1件是发明专利无效纠纷,G公司针对涉案专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无效请求,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宣告部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无效决定后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决定中关于继续维持权利要求有效的内容,要求重新作出审查决定。G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由于专利民事侵权判定要以无效行政案件裁判结果为依据,于是我们安排这5件案子同一天开庭。上午审理行政案件,下午审理民事案件,争取一天内把案子的脉络理清楚。”该案主审法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了协同审理的思路。2023年4月23日,按照合议庭安排,两家头部电器公司的专利之争拉开帷幕。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来说,由同一个合议庭审理多起专利的侵权民事和确权行政程序交叉案件并不是第一次,而已经成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以来长期坚持的做法。有评论表示,“二合一”审判模式是实现专利侵权民事诉讼与确权行政诉讼协同审理和标准对接的有益探索,可以有效缓解专利权人维权“周期长”等诉讼程序瓶颈问题,是国家层面知识产权上诉审理机制的显著优势。
新闻资讯
-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有了“绿色通道 07-22
-
2024生物制药企业专利保护与 07-22
-
2024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 07-22
-
备货夏上新抢跑618快手磁力引 07-21
-
北美豪门100T放弃英雄联盟只 07-21
-
2025年校服品牌推荐:最新权 07-21
-
第五大空调商奥克斯冲刺港股IP 07-21
-
品牌线上渠道销售困境与维权控价 07-21